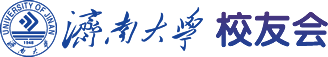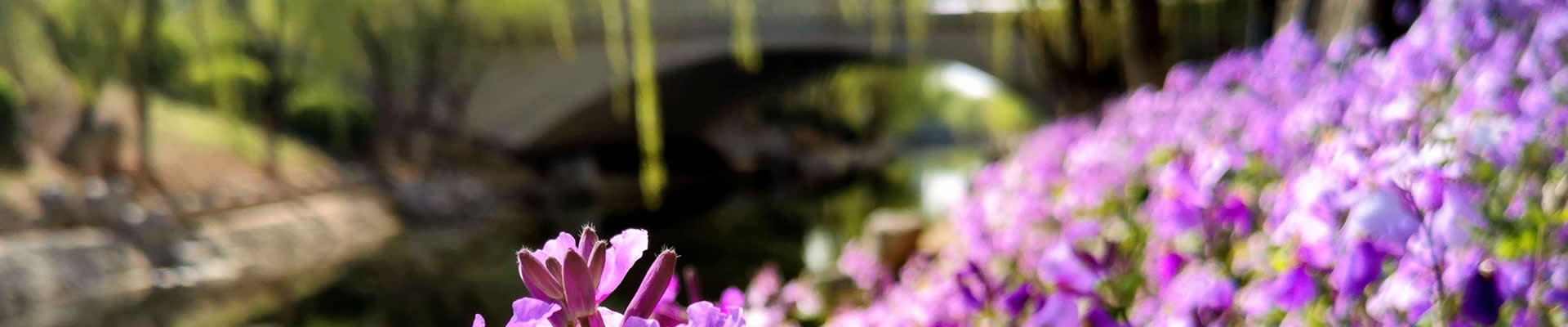生命常被比作一条河流,而我这条小河已经蜿蜒流过了许多站点。我在云南出生,在昆明度过童年,看着西南的红土高原读书、考大学,来到济南。济大这一站很长,我停泊到现在,已有一度春秋。
我曾任意让支流蔓延,伸向东西南北。上海的南京路和外滩是金色的,让人沉醉。厦门的树与海是透明的,散发出阳光的味道。而济大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灰的。
记得初到泉城的第一天是清晨7点钟,太阳还在伸着懒腰,整个城市安静地裹在薄雾里,K92路车带我穿越市区驶向济大。只记得窗外罗志祥的大幅广告频繁地闪进来,才消失就又出现了。公交车在薄雾里穿行,从客运站到济大是段安静而漫长的旅途。
最先看到的建筑,是济大的新西门,砖色的,灰扑扑地立在那里,有些呆气。说句老实话,我是有些失望的,理想中的济大,原来就是这样。
顺着紫荆路向前,满满的绿意迎面涌了过来,空气澄清许多,才稍微觉得好些。清晨的校园安静极了。甲子湖的荷花已经谢了,绿泉广场的喷泉也躲了起来。这里似乎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沉静。济大,似乎从未刻意想过让自己特别一些。
一年的本科生涯转瞬即逝。在这一年里,清晨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十教、十一教和宿舍间穿行。学校里各式各样的讲座和社团活动可以满足大多数人享受青春活泼大学生活的需求。二食、八食堂门口,饭点儿时候,空气中除了飘着饭香,还会飘来各种传单和社团活动的呼喊、吆喝,还有卖水果的大叔大妈,这里总是最热闹而匆忙的。太阳底下,各色展板突显出来,非常醒目。白色的、红色的传单躺在停放着的自行车的车筐里。卖水果大叔大妈的小摊儿永远那么诱人,黄灿灿的香蕉、金橙橙的橘子,还有苹果和葡萄。这儿也是济大校园里最灿烂的地方。
济南的春天总是短暂而急促,夏天则异常闷热,冬天的雪也远不及北国。但,秋天的济大校园,却是我的最爱。紫荆路的尽头,观霞桥旁那几株银杏,大概是最早染上秋色的,叶子依次由绿转黄,悄然变化,几乎无从察觉。某一天偶然望去,它们已经变成一幅写意画了。这些树有着柔和的轮廓和层次,浅浅的金色里镶着浓厚的金,但绿的痕迹也依然鲜活。每棵树都有着不同的色彩比例,又都半掩在同伴的树影里。桥旁是塑胶跑道和运动场,济大的钟楼在那头,一动不动,悄然引诱着桥这头的行人。待到秋意转浓,国际交流中心外墙垂下来的藤蔓植物变成红色,则又是一处佳景。致远路边的梧桐在深秋更是落叶缤纷,姿态妖娆。晚上的甲子湖畔变成了温柔的水乡,在昏暗的路灯的光晕里,教学楼的影像倒映水中,理智而庄重的线条随波光流动而变得柔和。一些安静的夜晚,甲子对岸会传来悦耳的箫声。在蒙蒙的夜色中隔水听箫,不知声源处是何人伫立,我尽可以让那些曼妙的想象在脑中肆意驰骋,没有人能看得到我心动的表情。
大多数时候的济大并不喧嚣,尽管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五六点的食堂总是很拥挤的,而且各个时间段内,仍有各种车辆穿行于学校的生活区中。校园广播里对时事政治关注的热度不亚于体育,各类鲜红的横幅和志愿服务等活动总是试图把济大的幽幽曲径镶上一些色彩。但,济大仍然是内敛的、自我约束的。
图书馆的阅览室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新书旧书散发出的墨香让人觉得安心。阳光透过茶色玻璃斜射进来,木质的桌面反射出一片橙色的光芒,我可以坐在这里静静地阅读或者发呆,直到太阳西晒。这里的感觉和气味,和济大是最接近的。
济大虽地处城郊,但校外却也热闹非凡。新西门外有繁华的夜市,东门对着郎茂山区,南门外是二环南路,车流交织成网,济大则身处其间。整个地区一到夜晚便沉浸在斑斓的霓虹灯世界里,而济大是灰色的。她就在那里。她可以欣赏活泼生动,可以接受大气华丽,也可以包容低调孤独。她无声息地包容了许多,然后将所有锋芒敛起,只释放出舒缓从容的气息。济大最吸引人的地方几乎从不是她的建筑、她的硬件。她所独具的,只是这沉稳雍容的气息。她总是不那么显眼,却处处找得到她的身影,至少在我的这条河流中,还时时倒映着她的倩影。